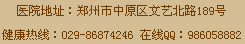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治疗手段 > 血管神经因子对早产儿脑损伤保护机制的研究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治疗手段 > 血管神经因子对早产儿脑损伤保护机制的研究

![]()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治疗手段 > 血管神经因子对早产儿脑损伤保护机制的研究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治疗手段 > 血管神经因子对早产儿脑损伤保护机制的研究
选自中华儿科杂志,,54(03)
早产儿脑损伤(braininjuryinprematureinfants,BIPI)是引起早产儿认知功能障碍以及脑瘫的首要病因,严重影响早产儿的生存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1]。近20年来,随着早产儿救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超早产儿的成活率明显增加(50%~70%),随之而来的神经发育障碍也大幅上升。大量研究显示至少有1/4的存活者发生脑瘫,而神经发育不良的发生率更是超过50%[2]。BIPI的病因非常复杂,机制也不十分清楚,多种病理变化均可导致早产儿神经发育障碍,根据发病机制分为出血性损伤和缺血缺氧性损伤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为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后者则表现为脑室周围白质软化(periventricularleukomalacia,PVL)。二者的发病率均与出生胎龄成负相关,由此推测,早产儿脑血管结构发育不成熟以及脑血流调节机制不健全可能是BIPI发生的病理基础。神经血管单元(neurovascularunit,NVU)是指由神经元、神经胶质和血管构成的体系,包括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周细胞、基底膜以及细胞外基质,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维持着神经元的正常生理功能以及损伤后的修复。血管神经因子是一大类可以作用于NVU,同时具有促进血管生成、调节血管重塑以及血脑屏障通透性,调节神经细胞代谢、促进神经细胞再生的细胞因子。这些血管神经因子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NVU,调节其结构和功能,在维持神经元正常生理功能和损伤后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就近年来早产儿脑血管发育以及血管神经因子在BIPI中对NVU的保护机制等相关进展做一综述。
一、早产儿脑血管发育与BIPI的关系
早产儿脑血管的发育包括血管发生和血管生成两种方式。前者是由血管内皮前体细胞或者血管母细胞经不断增殖形成新的血管,后者则是在原有血管基础上通过芽生的方式生成新的分支,形成更加成熟、稳定以及功能完备的血管网络。人类脑血管在妊娠20周后开始动脉化,妊娠24周从大脑前、中、后动脉发出长穿支,延伸到脑室边缘形成"小动脉终末区",维持脑室周围白质血供。短穿支在妊娠32~40周发育最活跃,主要供应皮层下白质。长、短穿支之间的吻合支在妊娠32周之后才逐渐形成,在此之前出生的早产儿,其脑组织小动脉之间缺乏有效的侧支循环,因此对缺血比较敏感。早产儿生发基质的血管生成尤其活跃,但是新生血管表面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和周皮细胞覆盖率较低,这种结构的特殊性被认为是生发基质容易导致机械性破裂和出血的基础。
新生儿出生后血氧饱和度明显上升而脑血流迅速下降。研究发现,新生儿出生后第1天,脑组织摄氧明显增加,这种表现在早产儿更明显,提示当脑灌注减少、贫血或血氧饱和度下降时,脑组织通过增加摄氧来满足其氧需求,即所谓的"贫困灌注"现象[3,4]。此外,早产儿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不成熟:调节范围较窄、不同个体之间以及同一个体不同临床状态之间差异较大,并且呈现"压力被动性血流调节",因此在低血压时容易发生缺血性损伤,而在血压波动或高血压时则容易发生出血性损伤[5,6]。
酪氨酸蛋白激酶抗体B2(EphrinB2)和B4分别由新生动、静脉内皮细胞表达[7]。Zhu等[8]根据这一特性,通过检测颅内EphrinB2和B4水平来明确大鼠缺氧缺血损伤后颅内血管正确的解剖分布,结果显示实验大鼠颅内EphrinB2和B4水平均升高,而假手术组二者的表达均无增加,因此认为,缺血缺氧性损伤可以诱导脑血管重塑,提示血管生成及重塑在缺氧缺血损伤后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主要的血管神经因子及其在BIPI中的作用机制
血管神经因子是指能够同时影响神经发育和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生物大分子,主要的血管神经因子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VEGF)、血管生成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neurotrophicfactor,BDNF)、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growthfactor,IGF-1)等。Kim和Chuang[9]研究证实在缺血后的纹状体、室管膜下区以及胼胝体区,VEGF水平明显升高。Ma等[10]进一步发现VEGF除促进血管再生外,还对神经细胞具有独立的直接保护作用。IGF-1则通过激活磷酯酰肌醇-3激酶(PI3K)-丝氨酸/苏氨酸激酶通路发挥其神经保护作用,减少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神经元凋亡[11]。据此推测,VEGF、IGF-1等血管神经因子可能在BIPI中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1.VEGF:
包括A、B、C、D以及胎盘生长因子(PIGF)5种亚型,对应3种受体VEGFR-1、2、3。VEGF在缺血后脑血管生成、神经再生及营养、细胞保护以及功能恢复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12,13,14,15]。研究显示,VEGF-A在卒中大鼠脑组织中表达增加,是介导脑组织小动脉生成的关键因子,使缺血后脑血管生成增加并减少梗死范围。阻断VEGFR-2则可以加重脑损伤,促进细胞凋亡,减少内皮细胞增殖[15],提示VEGF的促血管生成作用有赖于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特异性受体的紧密结合。Zhang等[16]认为VEGF在局部缺血脑组织中具有促进NVU微血管生成、抑制细胞凋亡以及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长等三大作用。因此,VEGF可以促进早产儿脑血管发育及神经细胞再生,减轻因血流波动或氧供不足引起的BIPI,改善其预后。
2.Ang-1:
Angs是相对分子质量为的二聚体分泌型糖蛋白,包含两个结构域:负责同型配体寡聚化的N-端卷曲螺旋结构域和介导受体结合的C-端纤维蛋白原样结构域。Angs包括Ang-1、Ang-2、Ang-3、Ang-4,均为Tie受体的配体。Ang-1由个氨基酸组成,定位于染色体8q22,全长1.5kb,可产生4种不同的剪接变体,分别长1.5、1.3、0.9和0.7kb。Ang-1在血管生成中主要通过旁分泌的方式引起Tie2磷酸化,进而激活Tie2信号通路,促进各级血管分支形成,促进细胞间连接、基质成熟以及功能完备,形成结构完整、功能成熟的血管网。因而,Ang-1主要在血管形成后期及损伤后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稳定血管内皮[17]。在脑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及周皮细胞均可分泌Ang-1。Ang-1对NVU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生理状态下加强NVU各细胞间的相互协调,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生成,改善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渗漏以及增强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18]。病理状态下拮抗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刺激内皮细胞迁移、增加血管结构稳定性,并且抑制炎症导致的血管通透性增加及神经细胞凋亡,同时在脑血管损伤后的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19]。
3.BDNF:
可与两种不同的细胞表面受体结合:酪氨酸激酶(Trk)B和神经营养因子受体(LNGFR)。TrkB是一种配体特异性受体,BDNF与其结合后可形成二聚体并发生自体磷酸化,通过Ras-ERK、PI3K以及磷脂酶C(PLC)γ活化后信号转导促进神经元存活和分化,同时也参与调节神经元的塑形和凋亡。LNGFR又称为p75神经营养因子受体,BDNF与之结合后可激活一连串细胞间信号通路,包括核因子κB、Jun激酶以及鞘磷脂水解酶,启动细胞凋亡。内源性BDNF是缺血后脑细胞存活和修复的重要介质。成年鼠缺血再灌注后2h,扣带回及额叶皮层BDNF水平升高%~%,24h后,纹状体的BDNF水平减少40%。Grade等[20]证实,在卒中后,表达TrkB的星形胶质细胞结合并隔离脉管系统源性BDNF,从而促进神经前体细胞从室管膜下迁移到缺血区。研究显示外源性BDNF也可以减小急性缺血后梗死范围,改善NVU结构,显著恢复行为能力。但是,该作用受到受体水平限制。除此之外,BNDF以及其他神经营养因子(如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营养因子3等)被证实可以促进少突胶质细胞增殖以及髓鞘形成。因此认为,BDNF在BIPI的修复中可以减少损伤面积,促进神经细胞分化增殖及神经纤维髓鞘化,提高患儿生存质量。
4.EPO:
是一个相对分子质量为的多效性细胞因子,最初因为其造血功能而被认识。氨甲酶促红细胞生成素(CEPO)是EPO的一种衍生体,由EPO经氨基甲酰赖氨酸残基修饰后生成,功能与EPO相似但不具备促红细胞生成作用。EPO及其受体EPOR在脑组织的生成主要是在妊娠期和生后早期,随后迅速降至成人水平[21]。EPOR有2种类型:分布于幼红细胞表面的同源二聚体以及与其他细胞因子受体配对形成的异源二聚体,前者主要介导造血反应,后者则具有重要的调节保护和促再生作用,尤其是对脑组织中的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22]。研究显示,EPOR转录在损伤后2h即达到高峰,并在较高水平持续6h,约12h后逐渐回落至正常水平。Liu等[23]研究发现,在PVL小鼠模型中,内源性EPO和EPORmRNA水平在脱髓鞘病变发生前会有短暂升高,在脑组织不同区域,其编码基因表达水平不同。而在正常对照组中,白质区EPO和EPOR水平极低,提示EPO和EPOR与脑白质脱髓鞘病变有关。另外,EPO还可以通过促进血管再生而降低神经元死亡、星形胶质细胞活化以及神经毒性物质水平,从而改善神经学结局和血脑屏障功能。Zhou等[24]在实验中发现,EPO主要通过促进连接蛋白(Cx)43磷酸化发挥对NVU的保护作用[25]。最近发现外源性EPO可以呈剂量依赖性地透过血脑屏障,并且通过多种机制保护神经元以及血管内皮细胞,同时抑制星形胶质细胞聚集[26,27],实现对NVU的保护[28]。在小鼠模型中,EPO和CEPO均能减轻脑白质损伤。对于早产儿PVL,外源性EPO或CEPO也具有显著的神经保护作用。此外,EPO还对损伤早期由VEGF介导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具有保护性调节作用。
5.IGF-1:
是一个相对分子质量为的多向性肽链,与多种促存活信号转导机制有关。IGF-1的生物学效应与其结合蛋白密切相关,生物体内至少存在6种IGF结合蛋白(IGFBPS),这些结合蛋白与IGF-1结合后可调节后者的生物学效应,具体取决于结合的方式以及效应组织。IGF-1在NVU的发育中扮演重要角色,脑组织中,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均广泛表达IGF-1。体外实验中,IGF-1被证实可以抑制谷氨酸盐、一氧化氮(NO)以及过氧化氢相关性细胞凋亡,保护感觉和运动神经元免遭兴奋毒性和氧化应激损伤。血脑屏障的微血管内皮细胞经氧气-葡萄糖剥夺处理后可引起缺血后IGF-1分泌增加,从而减轻神经元损伤[29]。通过药物抑制星形胶质细胞表面IGF-1及其受体,发现IGF-1的正常表达是星形胶质细胞遭受H2O2介导的氧化应激损伤后能够继续存活的关键,同时,IGF-1与胶质源性干细胞因子相互作用也是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应激损伤的重要因素[30]。
6.其他:
NO和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induciblefactor1,HIF-1)在脑损伤中的保护作用也被逐渐认识和进一步研究。在脑缺血早期,NO主要通过扩张血管以改善缺血局部脑组织氧供,减轻脑损伤。另外,多项研究证实NO与脑血流调节、神经元再塑以及神经递质的释放有关,同时可以促进未成熟脑组织的发育、减轻缺血缺氧或兴奋毒性造成的脑损伤[31,32,33]。HIF-1是热休克蛋白的一种,在脑组织缺氧后数小时内其表达即可增加。HIF-1可以调控多种基因的表达,以促进脑组织对低氧环境的耐受,通过增加葡萄糖转运及糖酵解增加神经细胞的生存能力,同时还可以调控脑血管张力及血管生成,进而促进脑缺血或再灌注后神经细胞的修复。研究还发现,HIF-1可以启动VEGF基因转录,促进VEGF表达,起到间接保护NVU的作用[34]。除此之外,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样生长因子、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均因其神经保护潜能而正处于进一步研究当中。
三、血管神经因子在BIPI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BIPI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级联反应,有多种血管神经因子参与其发病和修复过程。在这一病理过程中,细胞的死亡主要发生在3个阶段:首先是缺氧和能量衰竭,其次是再灌注损伤和自由基形成,伴随二次能量衰竭和神经细胞迟发坏死,第三阶段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等影响少突胶质细胞成熟、神经再生以及轴突形成过程,进一步加重原有损伤,或者产生新的损伤,或者阻止损伤后修复[35]。这是一个连续发生的"瀑布样反应",兴奋性谷氨酸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影响前体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和存活,氧化应激和自由基也是早期损伤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针对BIPI前两个阶段的干预手段相对有限,主要是通过降低脑细胞耗能来减轻神经损伤,均属于被动适应。在过去在数十年时间里,大量的致力于单独或联合应用多种神经保护药物的临床实验均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进一步的分析提示这可能归因于治疗靶点的过于单一[36]。NVU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神经元、神经胶质和脑血管之间相互联系及相互影响的重要性,为整体研究神经损伤及保护机制、寻找临床治疗的新靶点提供依据[37]。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局部脑缺血期间,NVU的首要改变是其结构完整性的瓦解以及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而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的损伤则是最终的结局[38]。提示NVU各个细胞组分之间的信号转导是保证大脑正常功能活动的基础,完整的神经保护应该同时包括神经胶质保护和血管保护,以增强所谓的大脑认知储备,弥补既往单纯营养神经治疗的局限[39]。
从各种血管神经因子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出,这些因子对NVU的保护作用贯穿BIPI的各个阶段。它们通过抑制炎性反应、改善血管通透性、提高神经元耐受性等各个方面避免NVU进一步损伤,同时通过促进脑血管生成、营养神经以及促进神经细胞增殖、分化等作用发挥其特有的神经保护作用,促进NVU成熟以及损伤后修复。此外,各个血管神经因子之间还存在互补或协同作用,进而共同促进NVU的损伤后修复,如EPO除自身的神经营养和保护作用外,还可以刺激BNDF的产生,二者之间存在协同作用;HIF-1同时可以促进血管生成因子(VEDF)的合成;VEGF在损伤早期刺激血管新生,Ang-1则促进新生血管重塑,改善其通透性等[40]。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上述血管神经因子在BIPI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如:Bain等[41]对VEGF亚型的作用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缺氧后的不同时期,VEGF-A和VEGF-C对模型鼠脑室管膜下神经胶质祖细胞产生的影响不同;Garry等[31]则对NO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为NO进一步应用于BIPI的治疗奠定了基础。同时已经开展了诸如亚低温联合氙气、亚低温联合EPO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等一些前期临床的组合性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40]。尽管如此,目前各种血管神经因子在BIPI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局限于动物实验。由于早产儿NVU的结构特点以及CBF的调节机制的特殊性,类似应用在BIPI干预中仍面临挑战。再者,各种血管神经因子均为生物大分子,不易透过血脑屏障,比如EPO的神经保护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这可能是因为只有较高剂量时EPO才能在脑脊液中达到有效治疗浓度[40]。其他血管神经因子可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第三,各种血管神经因子在体内复杂的作用和调控机制、联合应用时各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因子的有效剂量及使用途径等方面认识的相对欠缺也是限制其临床应用的重要原因。但前期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为BIPI的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随着基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临床研究的逐步开展,血管神经因子势必为BIPI的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更多精彩尽在中华儿科杂志
策划北京白癜风诚信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evwmh.com/zlsd/90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