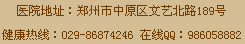第二节 苏珊?朗格的美学
一、苏珊·朗格简介
苏珊·朗格(SusannLangr,—),美国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家。她全面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卡西尔的艺术符号论,使符号论美学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鼎盛期,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科斯特拉尼茨说:“战后十年,在美国几乎没有一种艺术哲学比苏珊·朗格所阐述的理论占有更大的优势”。 苏珊·朗格的父母是德国人,后移居美国。她生于纽约,在美国接受教育并获得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乃狄克学院等校任教,五十年代后主要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哲学实践》()、《哲学新解》()、《符号逻辑导沦》()、《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哲学随笔》()、《心灵:论人类情感》()等。
二、语言符号与情感符号
1.符号是人的本质 朗格继承了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传统,反对先验的形而上学单纯从概念出发对艺术作抽象的逻辑推演,而坚持对各种艺术进行具体的经验分析;同时,她也不同意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放弃或取消对艺术作形而上研讨的倾向,认为哲学是美学和“整个知识大厦”的“框架”,所以应在经验分析基础对艺术作出哲学的概括。她的艺术哲学就是以卡西尔的符号论为基础,兼采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幻觉说等美学学说之长,所作出的哲学概括和综合。如她自己所说:“正是卡西尔——虽然他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位美学家——在其广博的、没有偏见的对符号形式的研究中,开凿出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则将要把这块拱心石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连接并支撑我们迄今所曾建造的工程。” 不过,苏珊·朗格的哲学构架同卡西尔的不完全—样。卡西尔是在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的框架内建立起他的文化批判哲学的,符号论则是他的文化哲学的核心。苏珊·朗格并不是从文化批判哲学角度去继承卡西尔的,而是把卡西尔的符号论作为她全部美学的基础,同时摆脱了康德先验沦的框架,并更多地为符号论输入了经验主义的血液。 苏珊·朗格认为每一时代的哲学的性质都是由这个时代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的。她说:“每个社会都用它自己的观念、它自己心照不宣的、基本的看事物的方式来迎接一种新的思想,那就是说,用它自己的问题,它的独特的好奇心来迎接一种新的思想。”她早在年就预言了符号论哲学时代将取代经验实证主义的时代:“人们已将—个新的哲学主题向即将到来的时代提了出来:那是—个认识论的主题,即对科学的理解,符号主义的力量将是这个主题的提示,就像感觉材料的终极性是先前一个时代的哲学的提示一样。” 朗格首先继承了卡西尔用符号来规定人的本质的思想,重申了使用符号是人的独有本性的观点。她说:“没有更高级的敏感性,没有更长久的记忆,或者甚至也没有更快速的联想,使人如此远远地高出于其他种类的动物,以至他能把这些动物都看成一个较低世界的外来居民:不,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言语的能力——才使人主宰地球。”她还说:“符号论是人们已认识到的开启精神生活的钥匙,而精神生活是人类独有的,它体现出高于纯粹动物性的水平。符号和意义形成了人的世界,这远远超过感觉的人的世界。” 2.符号与信号的区别
朗格也继承了卡西尔对符号与信号的区分。卡西尔认为动物已有复杂的信号或信号系统,但无符号使用能力,只有人才会使用符号。信号与符号的根本区别在于:“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与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的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则是‘指称者’。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朗格则对信号与符号的本质作了进—步的区分。她也把信号看成实在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即直接经验事件的一部分,而认为符号只具有间接指称、传达意义地概念功能。她指出:“在使用符号和仅仅使用信号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信号的使用是心灵的最初表现”,动物的“条件反射”属于信号的使用。人也使用信号,但是,“人不像所有其他动物,他使用‘信号’不仅为指示事物,而且也为代表它们”。信号用于当下存在的直接对象,符号则用于非当下存在的间接对象,“我们在我们自己中间使用某些‘信号’,它们并不指任何我们当下真实环境里的事物。我们多数语词并非信号意义上的记号,它们常被用于谈论有关的事物,而非用于引导我们的眼、耳、鼻去面对这些事物”,“在此意义—上使用的‘信号’,就不是事物的征兆,而是事物的符号了”。在朗格看来,信号与符号有相通之处,但在动物与人的不同使用中,信号就转变为符号了。这里,二者的主要区别是:(1)信号是直接的,是对当下存在的事物的指示。(2)信号是当下存在的事件的一部分,它引发并指令行动,“对于经验的观察者来说,它意味着某种显著特征的静止状态,它是事物的征兆”,同时它“是指令行动的某物或某种方法”,而符号则在事物之外,不是事物的替代而是指示的媒介,因此,它可以传达事物的某种内在含义。(3)信号只涉及感觉,符号则更多地诉诸概念,与理性密切相关。(4)信号只指示它所对应的具体特定事物,而符号则较抽象,可以指示不同事物,包含多种含义。(5)朗格还从构成要素上对信号与符号作进一步区分:“一般信号只包含三个基本方面:主体、信号、客体,而最一般地符号功能则包含四个基本要素:主体、符号、概念、客体。这样,信号意义和符号意义的根本区别就被逻辑地显示出来了。”这里符号结构比信号结构多了一个要素——“概念”,即意义。(6)正因为符号活动包括概念抽象活动,所以动物与人都可以使用信号,而符号则只有人才会使用。正如朗格所说:“理解符号的能力,即把关于感觉材料的每一事物都完全看成其所包含的特定形式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特质。”
朗格上述对信号与符号的区分表明,她认为从信号到符号的演变,是质的飞跃,是人类走出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人的符号活动是从信号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符号活动高于信号活动的根本特点在于符号活动已包含了抽象和概念活动,从信号到符号是从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感性到理性的转化。 总起来看,朗格的符号论在基本思想上并未超过卡西尔,但在具体论证上则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了,而且其论证过程的经验主义色彩比卡西尔更浓。 3.语言符号与情感符号的区别 朗格对卡西尔符号论更重要的发展是她关于语言(逻辑)符号与情感(非逻辑)符号的区分和论述。 卡西尔在论述语言与神话、逻辑思维与隐喻思维的区别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卡西尔认为,语言的“标准的逻辑概念形式”与神话或语言的“原始形式”,“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倾向”:前者“是以某一点为圆心向日益张大的知觉和概念范围的扩展”,即“导向概念的外延扩展”;后者“心灵的图景不是扩大而是压缩了”,“知觉的某些内容成为语言一神话的施力中心,成为意蕴的中心,而其他内容却依然站在意义的门槛之外”。他对这两种思维方式作了细致翔实的比较分析,并论述了人类早期语言与神话合一状态的分化过程,指出,“从一有语言开始,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力量:逻辑力量”,在语言进化过程中,“语词越来越被简约为单纯的概念的记号”,其逻辑力量日益扩大;同时,神话与原始语言中又分化、发展出另一种符号形式——艺术。”卡西尔还谈到语言符号的两种功能,他说:“我们理解现实不仅用普遍的概念系统的普遍原则去包摄它,也用具体的和个别的形象去直觉地感知它,这种具体直觉不能单靠语言获得,实际上我们普通语言不仅有概念的特点和意义,它还有直觉的特点和意义。我们普通词汇不仅是意义的符号,它们也充满了形象和特定的情感。它们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理智,也作用于我们的情感和想象。”这里,卡西尔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符号形式,一种是逻辑概念系统,—种是感情与形象系统(即非逻辑符号系统)。后一种方式发源于神话的隐喻思维,是一种先于逻辑思维,并成为逻辑思维根源的符号形式。朗格认为,卡西尔把哲学研究扩大到“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领域,“这样一种观点必将改变我们对人类心智的全部看法”。 朗格沿着卡西尔的思路,更为明确地区分了语言的逻辑符号和非语言的情感符号。她指出,人类语言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最初的语言是用来表示某些人类感觉对象的简单称谓或关系,是指向具体、个别、当下直接的事物的。以后这种单一的称谓分化为抽象与具体的两种意义。然而,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表达与交流,就必须把单个概念参与到综合使用之中,从而形成概念之间的一定关系。经约定俗成,遂使语言形成一定的语法、句法的逻辑系统。这种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朗格称之为“推理形式的符号体系”,其“符号作用即我说的逻辑表现,它表示各种关系”。朗格认为,人类语言从隐喻性的符号开始,逐渐扩大概念的范围,推理性的表达逐渐代替非推理性的原始符号,这“是人类思维和语言的正常发展过程”。朗格对语言符号体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惊人的符号体系”。因为“运用语言可以表达出那些不可能模仿和没有形体的东西,亦即被我们称之为观念的东西;还可以表达出我们所知觉的世界中那些隐蔽的、被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正是凭借语言,我们才能够思维、记忆、想象,才能最终表达出由全部丰富的事实组成的整体;也正是有了语言,我们才能描绘事物,再现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各种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进行沉思、预言和推理那样一种较长的符号变换过程”。语言还是人类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 但是,朗格也看到,语言推理的逻辑符号并非万能,也存在着局限性对“一些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东西”,“不能诉诸于逻辑的思维”的东西,语言的逻辑符号就无能为力。这些东西“不仅仅包括那些即时性的、无形式的和无意义的冲动体验,而且还包括那些作为复杂的生命网络的一个方面的经验”,即“有时我们称为主观经验方面的东西或直接感受到的东西”,也即情绪或情感所构成的人们的“内在生命”,它们“就像森林中的灯光那样变幻不定,互相交叉和重叠;当它们没有互相抵消和掩盖时,便又聚集成一定的形状,但这种形状又在时时地分解着,或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爆发为激情,或是在这种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对于表达这种“内在生命”和情感,“对于描绘这种感受,语言实在太贫乏了”,它“只能大致地、粗粗地描绘意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着的心绪、内在经验的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印象、记忆和再忆、超验的幻觉……的相互作用方面,则可悲地失败了”。一句话,语言的逻辑符号无法描绘、表达非逻辑的情感运动,这就需要另一种非逻辑的符号系统,这就是“情感符号”。 “情感符号”的组成因素不是语词,也缺乏像语言那样的各组成成分固定组合关系,因而不具备概念的逻辑推演特征。但是,它有一定的形式,可以借以传达、“领悟生命和感觉的过程”。它“是描绘而非推理的形式,它具有意义,却没有约定俗成的关系,从而不是把自己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表现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成分不是从逻辑上加以辨别,不是当作功能得以认识,而是当作性质得以感受”。这种非逻辑的情感符号体系是与语言的逻辑符号体系相对立、相对应的。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先于逻辑的概念的表达方式”的,或者说是在“逻辑‘之外’的”,“主观经验感情和愿望的领域”,然而它同样是人类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所应研究的对象。朗格有时把这种情感符号称为“表象符号’,并与语言符号作了对比,她指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在本质上是推理的,它有着永久意义的种种单位,它们又组成更大的单位;它所具有的种种确定的意义使界说和释译成为可能;它的内涵是概括的”;而表象符号“是非推理的和不能翻泽的,在本身的体系中是不允许有公式的,也不能直接传达普通性”,“它们作为符号的职能只是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它们被包括在—个同时出现的完整的表象之中”。朗格认为,艺术就是这种非逻辑的情感符号或表象符号的典型形式。 朗格的全部美学就是建立在语言符号同情感或表象符号的区分,以及对情感、表象符号特性的研究上。在这一方面,她把卡西尔的符号论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三、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苏珊·朗格在上述符号论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她独创的最重要的美学命题,即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个命题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她从符号论出发对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诸美学流派的批判吸收和综合改造。 1.艺术是情感的表现 朗格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一种非逻辑非抽象的符号、具有表现人的主观情感的功能。这里“情感”是广义的,指“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如果说语言逻辑符号“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周围事物同我们自身的关系”,那么,艺术作为情感和表象符号,“则是使我们认识到主观现实、情感和情绪”,这种符号“给这些内部经验赋子了形式,所以它们才得以被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把握到生命的运动和情感的产生、起伏和消失的全过程”。艺术这种情感和表象符号是“主观经验的自然形式被抽象到符号性的”这一高度时的产物,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人们就可以去“想象情感和理解情感的本质”。艺术符号表现了情感,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艺术符号来认识情感,这正是艺术的符号学价值和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朗格把艺术又“称为‘表现的符号体系’,以表明同推理符号即语言的本质区别”。在此意义上,朗格说,“‘表现性’是所有种类的艺术的共同特征”,这种表现性,即表现情感的特性,是朗格对艺术符号特性的重要规定。 2.艺术不是自我情感表现而是人类情感表现 朗格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不应是个人的瞬间情绪,不应将这种偶然情感作征兆性的宣泄,更不应是纯粹的自我表现。这里,她同卡西尔—样,对克罗齐、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美学有批判、有吸收。她吸收到表现主义的“表现”概念,但对艺术表现的情感内容作了新的解释。按克罗齐的说法,艺术即个人的直觉或抒情的表现,朗格认为:“纯粹的自我表现不需要艺术形式”,“以私刑为乐事的黑手党徒绕着绞架狂吼乱叫;母亲面对重病的孩子不知所措;刚把情人从危难中营救出来的痴情者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或哭笑无常,这些人都在发泄着强烈的情感,然而这些并非音乐所需的,尤其不为音乐创作所需要”。她还说:“艺术品的情感表现……根本就不是征兆性的”,“一个号啕大哭的儿童所释放出来的情感要比一个音乐家释放出来的个人情感多得多”,然而,这决非艺术的表现,人们决不会去欣赏,“因为人们不需要自我表现”。 与“自我表现”相反.朗格提倡艺术符号应是一种“能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换言之,艺术应表现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或情感概念。她认为人有两种值感形式,一种是主观情感:,另一种是“客观情感”,“主观情感蕴含在主体自身内,客观情感包含在非人格的事物中”。“客观情感”是主观情感的外化或对象化,是凝结在客体上的情感,这是一种人类普遍能理解、感受的情感,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概念或形式。艺术符号所应表示的正是这种能展示人的经验、情感和内心生活的动态过程及其个别性、复杂性与统一性的概念或普遍形式,也即表现出人类情感的内在本质。艺术一旦脱离了狭隘的“自我表现’,而展示人类普遍的情感形式,它“就成为一种表达意味的符号,运用全世界通用的形式,表现着情感的经验”。 朗格认为,艺术的“表现”就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可见的或可听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认识的形式”。朗格的“表现”不同于克罗齐、科林伍德的“表现”,是指用感性的形式来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这是一个把“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可见的形式”,“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朗格虽然直接借用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但却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她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表现性形式’,它并不是—种抽象的结构,而是一种幻象”,它“所表现出来的富有活力的感觉和情绪是直接融合在形式之中的”,是“直接呈现出来的”。在这里,情感与形式浑然一体,形式仿佛就是情感本身,“甚至可以从中感受到生命力的张弛”。朗格与贝尔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说的情感不是存在于主体一边的被激发出来的“审美情感”,而是一种存在于对象中的情感;她所说的形式也非空洞的结构关系,而就是包含着情感并与情感融为一体的感性形式。 3.艺术的表现是创造而非制造 在艺术创造问题上,朗格与克罗齐、科林伍德一样,秉承了浪漫主义的遗产。朗格认为,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或表现,是一个创造的活动和过程。她为了证明艺术符号活动的创造性,把物质产品的“制造”与艺术品的“创造”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工匠“制造”的产品或“盖起”的大厦,“仅仅是物质材料的组合,或者是为了人的需要对自然物质的—种修饰,它不过对现成的东西加以安排而不是一种创造”;艺术品则是“原来不存在的,它不是材料的安排而是情感的符号”,它是“运用人的最大概念能力——想象力来罗致他最精湛的技艺的创造过程”。就是说,艺术的“创造”是用想象力创造出现存世界所没有的新的“有意味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这就涉及到艺术抽象和幻象的问题。 4.艺术创造是对幻象的创造 朗格还吸收了古典的艺术幻象说和艺术虚构说。在朗格看来,各种创造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的抽象。她说,各种艺术有各自的特点,但“在作为‘创造物’这点上,它们却是相同的,对于—切种类的艺术来说,那被创造出来的‘生命的形式’都意味着同一种意思”,而“这种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而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情感”。就是说,艺术所创造的,是“广义的形式”,它既指事物的感性形状,又指“形成整体的某种排列方式”,即“最抽象的形式”,亦称“逻辑形式”。因此,艺术创造,在特定意义上就是艺术想象,就是创造出某种具有感性形态的“逻辑形式”,以表现人类的情感。艺术抽象不同于科学、数学、哲学的抽象,艺术家创造的形式,不取普遍的概念形态,而取具体、个别的感性形态,但它同时又显现出普遍的“逻辑形式”;从它中间可以“看到更为广义的形式——逻辑形式——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抽象的形式“又不是从体现它的艺术品中‘抽象’出来的”,而是普遍的逻辑形式就显现于个别的感性形态中。可见,艺术创造或艺术抽象,就是创造出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理性与感性水乳交融的具有具体感性形态的抽象逻辑形式。 朗格进一步指出,“艺术抽象的中心原则”是创造虚幻形象即“幻象”,即消除形象的实在性,切断其与现实(自然)的一切联系,使其非实在的外观表象突现出来。这也与科学抽象不同。科学抽象的惯用方式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获取抽象的概念或系统的关系模式,然后通过概念化的过程进行的”,而艺术抽象则“未必概括化”.而是“使它与自然脱离’,“创造一种感性虚象”。如绘画艺术,就是“创造出一种纯粹的视象,这就是那种只有表象而无其他的事物,亦即那种只能被视觉清晰地和直接地把握到的事物”,就是纯粹的感性外观和幻象,它已从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中抽象山来了。艺术创造和抽象出来的“幻象”,就成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 由于幻象是艺术符号(情感和表象符号)区别于语言符号的基本之点,又是艺术抽象区别于科学抽象的主要方式,所以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以此为基准,对各类艺术不同的“基本幻象”一一进行了分析。可以说,她是以不同形式的基本幻象作为艺术分类的主要依据的,从而确立了她独特的符号论的艺术分类原则。她认为,绘画、雕塑、建筑三种造型艺术的基本幻象是“虚幻的空间”,是与现实空间根本不同的、从现实空间中“抽象”出来的艺术空间,它诉诸于视觉,不过这三种艺术的虚幻空间又各有特点;音乐艺术的基本幻象是“虚幻的时间”,它是从现实时间中“抽象”出来的艺术时间,它直接作用于听觉的特殊的声音运动形式,同人的内在生命律动相吻合;舞蹈艺术的其本幻象是“虚幻的力”,它是不连续的“虚幻时间”中呈现于视觉的“虚幻空间”,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力的呈现与表象,是从实际的力的体系中“抽象”出来的,与人的内在生命力相合拍。诗比较特殊,诗用的是语言符号,但诗的陈述是非现实的陈述,诗的语言起了变化,它只充当一种材料,用以虚构经验与往事,创造真实的意象以超越语词本身而能表现人类的情感,诗用浯词创造出与现实隔离的虚幻形象。戏剧实质上也是一种诗艺,只是一般诗是回忆的模式,是“过去时”的虚象,而戏剧则是命运的模式,是“将来时”的虚幻形象。虽然这里朗格用基本幻象来划分艺术类型的方法并不完善,特别是在论及诗与戏剧时更显得牵强附会,捉襟见肘,幻象原则也未能贯彻到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她始终如一地强调子艺术符号的创造性,即创造出“脱离自然”的、非现实的幻象和感性外观,而这具体的感性形式又能表现出普遍的人类情感的“逻辑形式”。 以上几点,就是朗格关于“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的核心定义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她符号论美学的主要观点。
四、生命形式与艺术直觉
朗格美学虽然吸收了形式主义的成分,但仍然属于浪漫主义以来的“古典美学”的范畴。她的整个体系明显身透着经典的有机论美学色彩。其生命形式概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生命形式”是朗格美学中与“情感”概念处于同一等级的另一核心概念。它在朗格美学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1.情感形式即生命的逻辑 什么是“生命形式”?从朗格的全部著作来看,生命形式是同人类情感的普遍形式相近的概念。她有时甚至把两者混合或替代使用。如前所述,朗格所说的“情感”是广义的情感,“亦即任何可以被感受到的东西——从一般的肌肉觉、疼痛觉、舒适觉、躁动觉和平静觉到那些最复杂的情绪和思想紧张程度,还包括人类意识中那些稳定的情调”。显然,这是指作为—个生命有机体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感受或感觉。而在谈到生命形式时,朗格正是从这种广义的感觉、感受能力出发的。她说,“最基本的感觉”是“当整个有机体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时,机体内部生命节奏的自由流动或间有的中断”,而有专门感觉器官的高级有机体就产生了专门的感觉与确定的情绪,产生了更敏感复杂的主观直觉能力。她强调,“感觉能力并不是生命活动的结果,而是组成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感觉能力就是生命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生命本身也就是感觉能力”。这样,人的感觉、感受、情感、情绪等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了。因此,“当我们能够意识到情感和情绪是非物理的组合,而是精神的组成成分时,它们在我们眼里仍然是某种与有机躯体以及这个躯体的种种本能相类似的东西。事实上,它们看上去就好像是那生命湍流中最为突出的浪峰。因此,它们的基本形式也就是生命的形式,它们的产生和消失形式也就是生命的成长和死亡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而决不会是那种机械的物理活动形式,它们(即各种情绪和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组合也就反映了生物存在的方式”。可见,在朗格看来,情感、情绪就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情感、情绪的消长形式也就是生命活动的形式。艺术的本质既然是创造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那么,也就是要创造与生命形式同构、对应的符号形式。据此,朗格提出了她的艺术应创造生命的逻辑形式的理论。她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它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这里,朗格把“情感的形式”与“生命的逻辑形式”基本上等同起来了。 2.生命形式的特征 朗格不仅提出了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即生命的逻辑形式的论点,而且深入探索了这种牛命形式的基本特点,将之概括为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和不断成长性这样四个基本特征。她认为,这四个特征可以“把一切具有生命的事物与无生命的事物区别开来”。(1)有机性。“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有机体,它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有机体内有机活动的特征”。即处在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2)运动性。“一个生命的形式也是一个运动的形式”,它“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存在”,机体最基本的”生命感觉”便是对于它的持续性和变化性之间的辩征过程的感觉,这一辩证运动过程构成“情感生活”的基础。但生命体的运动不同于物理运动,它“包含着—种持续性结构,而这种结构又是由各式各样互相之间的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活动组成的”,这些活动本身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有中心的系统,是机体每一活动成分不断消亡与重建的过程。(3)节奏性。生命运动的持续性源于“变化式样的节奏性”,节奏性不独生物有,但有机体的生命节奏“主要是与机能有关而不是与时间有关”,“节奏的本质不在于周期性,而在于连续进行的事情所具有的机能性”,即由生命体机能构成的有节奏运动。(4)不断成长性:生命总处在不断生长与消亡的过程中,在高级机体中,“这些过程具体就是情感、欲望、特定的知觉行为等等”,就此而言,生命形式应有“那种随着它自身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长活动和消亡活动辩证发展的规律”。朗格认为,人作为高级生命体,其机能“都是从一种更加深层的情绪中进化而来”,但“仍然能够展示出这些深层情绪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它的能动性、不可侵犯性、统一性、有机性、节奏性和不断生长性。这些特征也就是一种生命形式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就是说,人的深层情绪和生命活动同样具有上述四个基本的逻辑形式。 3.艺术表现形式与生命逻辑形式之间存在着象征性联系 既然艺术应当表现人的情感、情绪,展示人的生命形式,那么,就应当按照上述生命活动的四个特征,也即生命的基本逻辑形式来进行艺术创造。所以朗格认为:“如果说艺术是用一种独特的暗喻形式来表现人类意识的话,这种形式就必须与一个生命形式相类似,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关于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都必须在艺术创造物中找到。”她认为,在艺术的表现性形式与生命的逻辑形式之间存在着“象征性联系”,艺术“可以用无数的手段去创造或加强这种‘生命的形式’”。这种“象征性联系”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逻辑形式的“同构性”。她说:“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要自觉运用这—原则,具体来说,就要在创造艺术的幻象时遵循生命形式的规律。譬如绘画,运用线条在所创造的虚空中既表现运动,又表现静止,创造出一个“空间一时间”性的形式,成为“表现持久性和变化性之间辩证关系的形象,即呈现出生命活动的典型特征的形象”。再譬如构思画或诗,应在形象结构中贯彻生命有机结构的原理,以达到有机整一性,使之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如硬要将它的各构成成分分离开来,它就不再是原来样子了——整个形象也随之消失了”。由此,朗格总结道,艺术结构与人的高级生命结构(情感与人性)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或同构性)使艺术作品“看上去像一种生命的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因此,“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地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 4.艺术作品应具有“生命的意味” 朗格认为,成功的艺术品应当具有“生命的意味”。一方面,作品本身像高级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特有的情感、情绪、感受、意识,等等”,另一方面,它可凭借与生命的同构性“传达”出“生命的意味”,换言之,“生命的意味是运用艺术将情感生命客观化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才成为“符号”,艺术是“由全部幻象,即由艺术符号排列和组合起来的幻象”来传达、表现人的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的。 5.艺术知觉是一种直觉 朗格认为,艺术知觉“是一种直觉”,“一种洞察力或顿悟能力”,“而不是一种推理性的思辨”。 这样来规定艺术直觉,是朗格以前许多人都已经作过的。朗格与众不同之处是她把这种非推理性的直觉、顿悟能力看成是“一种基本的理性适动”。她的这一观点是在形形色色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直觉论,特别是克罗齐与柏格森的直觉沦的基础上提出的,当然在批判过程中也有吸收。她指出,克罗齐与柏格森尽管理论上有许多分歧,但是有一点共同之处,即“他们都承认一点,这就是:直觉不具备理性的特点”,他们都认为,“为了提高直觉的价值和地位,就必须反对逻辑”。朗格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他们是在逻辑(理性)认识与直觉(感性)认识两种“方法”中制造对立。对此她批评说:“但实际上这种对立并不存在——因为直觉根本就不是‘方法’,而是一个过程。直觉是逻辑的开端和结尾,如果没有直觉,一切理性思维都要遭受挫折。”这里,朗格把直觉看成理性思维的基础,认为逻辑思维过程不能不伴随着直觉,而且思维的结果也应是一种直觉,即“逻辑性的直觉或顿悟”。这样,她就从认识沦上消除了直觉与逻辑、理性思维之间的僵硬对立,克服了克罗齐、柏格森直觉沦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得出了直觉是“最基本的理性活动”的结沦。 那么,直觉到底是什么呢?朗格说,直觉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导致的是一种逻辑的或语义上的理解,它包括着对各式各样的形式的洞察,或者说它包括着对诸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或认识……直觉只与事物的外观呈现有关”;“它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特殊的天才对现实存在的一种神秘的直接触知”(这是针对克罗齐和柏格森而言的)。与此同时,她也有批判地吸收了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中直觉与经验密切相关的思想,认为直觉的表现“就是基本符号的创造过程”,直觉形式的意象“是一个象征了这种经验的一个符号”;并强调,“只要人们把直觉当成远离任何客观联系的东西,那么,无论是它的变化还是它与理性、想象,或任何其他非动物性的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就都无法研究了”。 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地描述一下朗格心目中的“直觉”的涵义:(1)直觉是对事物“外观”的一种洞察过程;(2)它是对事物“外观”的逻辑形式的一种把握与洞察;(3)它同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经验密切相关,并且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4)它对事物外观与形式的洞察是直接的、顿悟式的,不假道于概念和推理;(5)但它并不神秘,它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并参与理解活动,因此属于人的基本理性活动;(6)它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开端,又是其结尾。朗格的这种“直觉”可以看成是理性的直觉。 朗格认为,在艺术中,直觉就是艺术知觉。她说:“当我们欣赏一件富有意味的艺术品时,那种时时参与到理解活动之中并构成了推理活动的基础的直觉就立即变成了艺术知觉。”艺术知觉是通过艺术符号对人类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洞察,是对艺术品“生命的意味”的顿悟。她说,“对艺术意味(或表现性)的知觉就是一种直觉,艺术品的意味——它的本质或艺术的意味是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直觉能力就是“用来认识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所体现出来‘情感生命’”。而对情感与生命形式的认识或知觉是经过由艺术幻象组成的艺术符号来进行的(虽然艺术的符号与其所表现的生命形式是融为一体的),在此意义上,“艺术直觉是一种判断,而且是——种借助于个别符号进行的判断”。总而言之,“艺术知觉是—种直接的、不可言传的,然而又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直觉”。
由于艺术直觉是对“生命意味”的直接把握,所以它对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至关紧要的。艺术家如果缺乏这种直觉,他就无法创造幻象符号——“有意味的形式”来表现、传达这种直觉;观赏者若缺乏这种直觉,面对优秀的艺术品就会茫然无知,根本无法发现和体验艺术符号背后的生命形式的律动。也正因为艺术创造和欣赏都离不开直觉,所以优秀的艺术品对人们(包括艺术家与观赏者)的审美直觉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朗格说:“艺术品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形成了我们关于情感,关于视觉、听觉和实体的概念。它把想象形式和情感形式一起呈现给我们,就是说,它所澄清并组织的就是直觉本身。虽然艺术品并不能导致自觉的理性思维(推理),但是,它所以具有一种启示力量,并能激励一种在理智上感到深刻满足的情感,其原因就在这里。”
相关阅读:
1|当代西方美学概述
2|表现主义美学(上)
2|表现主义美学(下)
3|英国形式主义美学
灏忓鐧界櫆椋庤兘娌诲ソ鍚?鐧界櫆椋庡灏戦挶鑳芥不濂?
转载请注明:http://www.evwmh.com/hlzs/82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