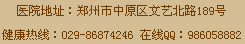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症状表现 > 我是谁带你深度探索我的秘密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症状表现 > 我是谁带你深度探索我的秘密

![]()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症状表现 > 我是谁带你深度探索我的秘密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症状表现 > 我是谁带你深度探索我的秘密
本文已经经过作者授权转载,原文出处:宇宙密码(e)
人类普遍地对一件事情无知,而这是一件最有必要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怎样正确地生活,怎样去照顾自己的灵魂并且使它尽可能地完善。还有,人们对这种无知普遍地是视而不见的。——苏格拉底
每个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成为自己。
年前,伟大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追问:“我是谁?”与之相关的还有两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苏格拉底说:“人类普遍地对一件事情无知,而这是一件最有必要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怎样正确地生活,怎样去照顾自己的灵魂并且使它尽可能地完善,还有,人们对这种无知普遍地是视而不见的。”
当然,苏格拉底是一个例外,即使他不拥有这种最高深的知识,但他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他知道自己对它是无知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尔斐的神谕会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明白,“我是谁”是人类自身最重大的问题。
1.我是谁?
2.我从哪里来?
3.我要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哲学的终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考验人类智慧的终极问题!
不信,你可以上百度去搜,看看那些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回答,有哪个能够真正令你信服或者满意?
佛教禅宗有个参了千年的话头——“念佛是谁”(念佛是我我是谁)——这是一个很多学佛人不敢面对的问题,是验证佛教徒是否开悟的终极问题。自古以来,能够参透的当真是凤毛麟角。
当然,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圣人孔子、神人老子无疑是知道答案的。他们分别用《易传》和《道德经》,系统而完整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如果你读过并且读懂了这两部经典,你完全不必再继续往下看。因为,我的回答显然要“小儿科”得多。
有“华语世界首席身心灵作家”之誉的张德芬,在40岁那年,受到这三个问题的启发与指引,辞去高薪的工作,专心研修新时代的各类心灵课程,然后写出《遇见未知的自己》,《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活出全新的自己》和《重遇未知的自己》等“身心灵成长四部曲”畅销书。这四本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讲述了同一个真理。那就是——
“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
那么,这个自己到底是谁呢?在《重遇未知的自己》中有一个专辑是《找出“我是谁”》。张德芬用7篇文章来阐述了这个问题,但她给出的答案是——
“我是谁”其实没有答案。
“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句话,我参了整整四年,并且在我写了整整篇关于纸牌的文章之后,我才终于有了惊鸿一瞥的了悟。
从前,我以为我很了解自己,我以为每个人都很了解自己。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我越来越深地领悟到苏格拉底的那句至理名言——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的确,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1
这不是我
你是谁?
尼采说:“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
你是谁?
尼采说:“你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使脱去了七十乘七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
你究竟是谁?
好吧,想要知道“我是谁”,先来了解一下“我不是谁”。
我不是一具身体
不止是你我,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就是自己的身体,甚至一些非常有智慧和有灵性的人处于恐惧和痛苦中时,也这样认为。
我的老师彼尚说,这样想并没有对错,只是,无论何时,当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身体时,就会忘记自己的“真我”所拥有的全部力量。
一些有过“出体”经验的人,会真实地体悟到“我不是一具身体”,但绝大多数人把自己等同于身体,并与此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而事实上,身体只是供奉我的一座神殿。身体会有毁损、衰老以及死亡的那一天,但我不会。
我不是各种身份
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在家里,我是儿子或女儿、孙子或孙女、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等等;在外面,我是朋友、邻居、亲戚、同事、领导或下属等等。
我在各种身份之间周旋、忙碌、纠结、沉醉,披星戴月,风雨兼程,饱经尘世风霜,尝遍人间冷暖,鞠躬尽瘁,无悔无怨。我以为,这就是我。
不,这不是我。
这只是我在这一世被贴上的标签,这只是我在这一世所扮演的角色。
我不是我的大脑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随之而来的此起彼伏的情绪。你无法停止思考,不断地跑到过去和未来;你也无法控制情绪,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无边的旷野狂奔。
你说,“我思故我在”。你把自己等同于你的大脑。你以为你就是那个思考者。但很有可能的是,你误解了笛卡尔的这个哲学命题的真正含义。
假设一下: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个思考者,那么“认为你是那个思考者”的你,是谁?如果你看见自己在哭,那么“看见自己在哭”的那个你,是谁?
我不是我的故事
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并且,我们对这些故事是如此的认同和执著,即使这些故事令我们耿耿于怀、痛不欲生,我们仍然紧紧抓住不放,仿佛那是我们的命根。
我曾经对一个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女孩说:“放下你的故事,那些只是故事,不是你。”她居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没有我的故事,我还是我吗?”
《当下的力量》的作者艾克哈特·托尔说,他曾经处在一个持续性的焦虑状态,其间穿插着自杀性的沮丧。30岁前的一天凌晨时分,他在一阵极端的恐惧之中惊醒过来。黑夜的死寂,暗室中家具模糊的轮廓,远方传来的火车噪音——这一切让他感觉格外的疏离、敌意、而且了无生趣。他对世界升起了一股很深的厌离之情。“我活不下去了,我受不了我自己。”这个念头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突然他觉察到这个念头的奇特之处。“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我受不了我自己,那么必然有两个我在:就是‘我’和我所受不了的‘我自己’。他们之中只有一个才是真的吧?”
艾克哈特从此开悟。
灵性导师拜伦·凯蒂有一本畅销书叫《没有你的故事,你是谁》。她在开悟之前曾经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抑郁症中。她卧病在床,狂怒与绝望日甚一日。最后,她住进了一个专门治疗患有饮食紊乱症的女性收容所里。有一天,她醒来,发现自己所有的痛苦都不复存在了。她觉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他人或事情总是执著于一个特定的想法,只要这个想法存在,它就会编造出无数个故事来支撑它的真实性。当你不相信这个想法和这些故事时,痛苦便结束了。
记住:那些让你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欲生欲死的都不过是你自导自演的故事,那不是你。
我不是潜隐人格
在“欧林资料”《活在喜悦中》这本书中,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潜隐人格”。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和身份,这些我们可以称为潜隐人格。这些角色存在于所有人之内。比方说,也许有个部分的我是鲁莽而冲动的,而有个部分则是小心谨慎的;有个部分的我是温柔而浪漫的,而有个部分却是粗暴而冷酷的;有个部分的我是博爱无私的,有个部分却是狭隘自私的;或者我有个部分是充满焦虑的,总在制造未来的恐惧;或者我有个偏执的部分,老是揪住一些痛苦的往事不放。
这些不同的人格常常让我感觉分裂。他们在我的内心不停地争吵,一个让我朝东,一个让我往西,一个让我向南,一个让我去北。我对自己有时欣赏、有时痛恨,有时自怜、有时自责,有时爱慕、有时憎恶。因为,我以为这些都是我自己。
不不,这些都只是我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我。
我不是种种幻觉
我的纸牌老师罗伯特说,生活中真正的大师是能够透过幻相的面纱,拨开迷雾,看到问题核心的人。
在著名的《与神对话》系列之《与神合一》中,讲述了“人类的十个幻觉”。这十个幻觉是人类在最早的地球经验期间,创造出来的很大、很具影响力的幻觉。而我们每天都还在创造出无数的较小幻觉。
由于我们是如此地相信它们,因此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容许我们将这些幻觉实践的文化故事,而使得这些幻觉得以成真。这十个幻觉以及相应的文化故事是:
1.需要的幻觉——神是有议程的。
2.失败的幻觉——生命的结局是可疑的。
3.分离的幻觉——你和神是分离的。
4.不足的幻觉——物质是不够的。
5.必备资格的幻觉——有些事是你必须做的。
6.审判的幻觉——如果你不去做,你是会被处罚的。
7.定罪的幻觉——那处罚是你永不得超生。
8.有条件的幻觉——所以,爱是有条件的。
9.优越的幻觉——由于了解并且合乎那些条件,使你优于其他人。
10.无知的幻觉——你不知道这些都是幻觉。
这样的文化故事是如此地铭刻在我们累生累世的记忆中,以至于我们现在完完全全地活在其中,并信以为真。
除非揭开这些幻觉的面纱,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够忆起——我是谁。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将这份“我不是谁”的清单无限地罗列下去。
总之,凡是你能看到、听到、想到的都不是你。
凡是你能看到、听到、想到的都是你的“小我”。
艾克哈特·托尔在《新世界——灵性的觉醒》中这样描述“小我”:
很多人对于他们脑袋里的声音是如此的认同——那个不间断的、不自主的、强迫性的思想续流,还有随之而来的情绪——我们可以形容这些人是被他们的心智占据的。如果你对此毫无觉知,就会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思考者。这就是小我的心智。我们称它为“小我的”,因为在每个思想——每个记忆、阐释、意见、观点、反应和情绪里,都有一个自我感(小我感)在其中。从灵性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无意识。你的思想,你心智的内容,当然是被过去所制约的,过去是指:你的教养、文化、家庭背景等。你心智所有活动的最核心包含了一些重复和持续的思想、情绪和反应模式,这些都是你最强烈认同的。这个实体就是小我的本身。
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当你说“我”的时候,其实就是小我在说话,而不是你,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它包含了思想和情绪,还有一堆你认同为“我和我的故事”的回忆,还有你不自知而习惯性扮演的角色以及一些集体的认同,像国籍、宗教、种族、社会阶级、政治立场等。它还包括了个人的认同,不仅是认同于个人拥有的东西,还包括个人意见、外表、长久以来的怨恨,或是关于你自己比别人好或是不如别人,还有自己是成功或失败的概念。
在全世界教授“奇迹课程”和“轻而易举的富足”课程的彼尚·安裘密,把小我比作我们养的一条小狗。他说,小我并非与生俱来,随着社会集体意识对人的影响,在人两三岁的时候,小我发展起来。它是一个基于恐惧而形成的分裂的思想。我们喜欢小我就如同喜欢小狗一样,为它系上狗链,并将狗链永远地扣在手腕上,如同一副手铐。
而我更喜欢《零极限》的作者、“荷欧波诺波诺”疗法的推广者修·蓝博士的解释:
没有所谓的小我。你知道吗?没有小我,那只不过是些数据而已。当然,数据会自己开口说话,数据会把自己称作小我——但其实根本没有小我。它只不过是些数据的累积罢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有的只是些数据。数据在说话,而且数据通过你来说话,结果你就失去了对于生命的掌控。
亲,看懂了吗?不论是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还是正在写这些文字的我,都只是小我——不,或者说,都只是数据。
这才是我
我有一个打小就很敬仰的解放军叔叔——我父亲的发小。他在部队一直干到团长,直至退休。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退休之后,他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曾经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选择基督教,而不是佛教?”
他严肃而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讲了很长一段,大意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研究了几乎所有宗教,只有基督教解决了他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问题。
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的师兄,也是我的初恋情人,现在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一个已经获得30多项国家专利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年,他来复旦大学访问时,我们见了一面。
其时,他已经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饭桌上,他跟我侃侃而谈他的“天父”——那个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
我很好奇地问他:“真的有神吗?神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一只蚂蚁趴在人的身上,无论你告诉它人是什么样子,它都无法窥见人的全貌。我们就好比那只蚂蚁,趴在神的身上。
我的解放军叔叔和我的初恋情人变成基督教徒的事实,让我耿耿于怀了好多年。为此,我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圣经》、《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道德经》、《古兰经》等各家经典,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三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也始终没能领会神究竟是什么模样。
差不多所有古老的宗教和科学家对世界、宇宙的来源,都有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唯有《圣经》说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出于大爱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创造了人类。关于“创世纪”的故事,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详。如果你沉迷其中,很容易信以为真。我想这就是我的那位叔叔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之一吧。
佛教的宇宙观与基督教的“上帝造世界”、“地心说”、“日心说”截然不同,且与现代科学的发现越来越吻合。在佛教宇宙观里,人既非天神创造,亦非生物进化,而是由光音天的天神们演化而来。话说娑婆世界的形成过程已近尾声,大地甘泉密布、醇香甜美,光音天的天神们周身光明,驰骋游戏于天地之间。他们终究禁受不住大地甘泉香味的诱惑,慢慢地痛饮起来。由于他们阴性身体里摄入了越来越多的阳性地味物质,身体变得粗重,光明渐退,再也飞不起来,遂在地球安居下来。这就是佛教的人类起源说。关于这类故事,佛经上有详细记载,其精彩和逼真程度丝毫不亚于《圣经》上的故事。为此,我严重质疑那位叔叔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是否认真地读过佛经。
我承认,我一度被佛经、圣经上那些深奥而奇妙的故事吸引,也常常被那些智慧而美妙的经文打动。我熟读《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有的甚至能倒背如流。但我最终的收获是:对世间所有的宗教彻底释怀。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的那样——“我没有任何信仰,我不愿意属于任何宗教组织。”
因为,真理是无路可循的。没有基督教的道路、印度教的道路、佛教的道路、你的道路、我的道路。一个人要找到真理必须摆脱所有这些道路。所有宗教都是通过思维建立的,是人发明的。是人心创造了石雕的偶像供人膜拜,是人心创造了有组织的宗教及数不清的信仰。“要想弄清楚什么是真相,你就必须超越心智所创造的东西。”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我想,可能穷尽此生,我都无法知晓关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的绝对真相。因为宇宙的奥秘是如此庞大而复杂,以我现有的意识和进化程度,我是不能理解的。既然如此,我所能做的就是敞开——向宇宙和世界敞开,向真理和真相敞开……
如果你接触过以赛斯、欧林、《与神对话》、《奇迹课程》等系列通灵资料为代表的“新时代”思想,就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们是拥有肉体经验的永恒存在的灵体(灵魂、灵性、圣灵)。
这是我目前最能认同的关于“我是谁”的答案。
关于“我是谁”的解释,充塞于“新时代”数百万字资料的字里行间,令人目眩神迷,相当难以简明扼要地罗列出来。
简单地说,我们来源于宇宙(也称“一切万有”),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具有宇宙的全部属性。
我们只要搞明白三个问题,就基本能够知晓“我是谁”了。
1.宇宙是什么?
宇宙在各宗教上都被简化为一个像人一样的“神”,拥有“如来”“佛祖”、“上帝”、“天父”、“主”、“阿拉”等不同的称谓,以及不同的诠释。
他具备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特性,但并非被神化了的超人,而是世间一切的源头。所以,不如说他是以纯能量(纯意识)的形式存在的,一个无形无相的创造者(造物主)。
他就是佛家所谓“真空生万有”的那个“真空”,道家所说“道生一”的那个“道”,儒家所曰“无极生太极”的那个“无极”,《圣经》所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个“神”。
理解这一点,我就理解了《金刚经》中所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深刻含义,理解了我的初恋情人所形容的“神”的真正模样(他根本没有模样)。
2.宇宙为什么要创造我们?
你不妨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一开始,只有宇宙存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宇宙无法认识他自己——因为他就是所有的一切。因此,他是不存在的——当没有其他东西存在的时候,宇宙也就不在。
就好比你乘宇宙飞船,周围没有任何星球或其他,你知道你在前行吗?当没有其它参照物时,你无法知道你在干什么,也无法知晓你是谁。
如果你自己在脑袋里曾有过任何梦想,你想得天花乱坠,却无法具体表达梦中的景物时,你便能体会宇宙他老人家“当年”的痛苦了。
现在,再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下:他那个无边无际的大脑袋里,升起了无穷无尽的梦想……他想得头痛欲裂,他内在的每一“念”,都渴望爆发出来体验形形色色的生命。最后,宇宙终于“爆炸”成无尽数量的比他整体小的单位。这些能量单位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
就这样,为了彻底地认识自己和经验自己,宇宙将自己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于是,有了天地万物和人类。
《与神对话》里,神(也就是宇宙)把这形容成——“是一个和你们的科学家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全然符合的灵性事件。”
3.我们具备宇宙的哪些特性?
①我是纯能量(纯意识)
由于宇宙是纯能量,我们来自于他,所以我们的本质就是一种纯能量,或者说纯意识。这是一个具有无穷可能性和无限创造性的场。由于它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又是纯粹的愉悦。能量的其他属性为纯粹的知识、无限的寂静、完美的平衡、坚不可摧、朴实无华以及至快至福。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质特性。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自性”(明心见性的性),佛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②我是空无
跟宇宙最初一样,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存在,所以我是不存在的,是空无。但是,这个“空无”不是没有,而是“空中生万有”——一切可以从中生出!当我这一世的人生结束了,我离开身体,回到空无。然后,这一生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到了我的灵魂档案里。下一世,我又来到一个身体里,开始另一个人生。这时,无又生出有。但本质上,我还是无。
③我是无限丰盛
在各种灵修课程中,我们会经常听到“我是丰盛的源头”或“我是圆满俱足的”这样的说法。这也是纸牌系统中方片7所呈现给我们的功课。除非你能够认识到你本然的状态就是无限丰盛和圆满俱足,你不“缺少”任何东西,否则,任凭你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丰盛和圆满。因为,你从宇宙那里分离出来,就是要来体验“不丰盛”和“不圆满”的!
④我是爱
爱是什么?克里希那穆提说,“这个字眼早已被世人所败坏了,所以我一直不怎么爱用它。”世间每个人都在谈论爱,每一份杂志、报纸以及传教士都不停地谈着爱。然而,我们真的明白爱是什么吗?
爱是宇宙的本然状态。爱是终极的真相,也是唯一的、所有的真相。如果要认识什么是爱,就必须有与之相反的东西。所以,宇宙创造了爱的对立面——每样不是爱的东西,现在被称为“恐惧”的东西。只有当恐惧存在的时候,爱才可存在为一件可能被经验的东西。
所以,克氏说我无法定义爱是什么,但我知道爱不是什么。“恐惧不是爱,依赖不是爱,嫉妒不是爱,占有控制不是爱,责任义务不是爱,自叹自怜不是爱,不被人爱的痛苦不是爱。”
爱是什么?爱就是你,当你记起自己真正是谁的时候。
⑤我是创造者
宇宙为了经验自己创造出无数个“我”,因此,他也赋予所有的“我”同样的创造力,以创造出万事万物,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彻底地体验他自己。
因此,一个最深的宇宙奥秘就是:生命并非一个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并不是在发现我自己,而是在重新创造我自己。所以,不仅要去弄清我是谁,更要去确定我想成为谁。
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虽然可能并不知觉。创造的工具是:思想、语言和行动。创造的过程包括相信或知晓。我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无论我相信什么,就会呈现什么。就像《与神对话》里神告诉我们的那样——
“你在你世界里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你对它的想法的结果。你想要你的人生真的‘起飞’吗?那么就改变你对它的想法。思想,说话,并且行动,如你是的神的模样。”
许多人把生活比作一场梦,其实它更像是一部电影:你的信念系统是剧本,你是制片人和导演,然后你选择主角或群众演员的角色。
⑥我永远不死
即使在科学家那里,这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发现:“当我们的肉体死亡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死亡。人的灵魂是不朽的,灵魂能在肉体生命结束后继续活着。”他将这段神奇的经历和这个惊人的发现写成了书,这便是风靡全球的《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启示》。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维克森林医学院大学教授兰萨声称,从量子物理学角度出发,有足够证据证明人死后并未消失。他提出生物中心论支持自己的论点,指称是生命创造宇宙,有意识才有宇宙的存在。兰萨的研究发现,人在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即物质元素处于停顿状态)时,人的意识讯息仍可运动,亦即除肉体活动外,还有其他超越肉体的“量子讯息”,或者说是俗称的“灵魂”。兰萨认为,当生命走到尽头,即身体机能尽失时,还会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开始。
关于我们的共同属性当然不止以上六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总之,这才是真正的我——一个圆满俱足、全知全能、永恒存在、生生不息的存有、灵体、灵魂、灵性(随便你怎么称呼))——宇宙这个神圣整体的一部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我在北京道德经艺术馆听韩金英老师讲丹道。韩老师有个学生叫小矫,不到20岁。当老师讲到“天场能量”的时候,小矫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人不能动弹。她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说,你现在感受的就是“一”的能量。接着,小矫变成了主讲,我们都听呆了。她说:“老师,我好像被定住了,自己变得无限大,只有一,我们都是一体的,小猫小狗和我们都是一体的……说出来的就都不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生死,观音、佛菩萨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一’,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老师说,这个孩子的自性本心被开启,看到了宇宙的实相,看到了《金刚经》中的“一合相”。
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的就都不是。除非有一天,我们跟小矫一样,开了天眼,进入时空隧道,看见真相。
所以,我说的都是错的,请不要相信。无论我说了什么,都只是抛砖引玉,引你回归自己,与你内在的真理重聚。
这就是我
每一个行为都是自我定义的行为。你的一切所思、所言、所行,都在宣布“这就是我”!——《与神对话》Ⅲ
除了罗伯特·李·坎普之外,斯蒂芬·福里斯特是我最喜欢的占星大师。他在《内在的天空》(占星学入门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学占星呢”中也提到了那三个闹心的问题。他的回答非常有趣。
他说,进行任何占星学的讨论时,只需10分钟,你多半就会碰到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的占星师告诉我必须面对这些事,为什么呢?如果我不想这样怎么办?”这些问题很快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斯蒂芬列举了两条“窗帘”模型。
“窗帘”一:我们是灵魂,是纯粹的意识、永生的存在,在此以肉体的形式不断转世,并慢慢地向一个与宇宙合一的状态进化。我们在出生之前有意识地选择了对我们的进化最理想的星盘配置。
“窗帘”二:宇宙是完全随机的。亿年前,氢云凝聚成了恒星,恒星开始烹调出更重的各种元素。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是一种电化学现象,完全依赖于大脑的生理机能。大脑死了,意识也就死了。
你看到这里面的区别了吗?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模型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说它完全相同。不管我们在头脑中如何构建和理解宇宙,宇宙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可以在头脑里不断地将各个概念的家具挪来挪去,一直到我们的脸变绿,但是还会碰到一样的心理难题——困难就是困难,不管我们的哲学观是怎样的。
我们究竟是灵魂还是肉体?
斯蒂芬的回答是:“从占星学的角度来说,标准答案是——管它呢。”
你可以选择这两个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们要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既然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创造一些接近真相的模型,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实际利益。
那么——好吧,我选择第一个模型。
在前面两章“这不是我”和“这才是我”中,回答了“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接下来该回答“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了。
在此之前,似乎还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
佛教认为:人间是剧场,轮回幻相相续,就像游戏通关,我们陷入到角色扮演中,上瘾难戒,明知是虚幻,却依然欲罢不能。所以,引导无明众生脱离轮回苦海、往生极乐世界,便成了诸位佛菩萨的大悲大愿和各个开悟上师们的使命职责。
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脱离人间、回归极乐”,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原本就是从极乐世界来到这里的啊!
没错,人间是剧场。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演一场戏。至于这场戏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全由你说了算。你是导演兼编剧,同时也是演员。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来这里是要玩一个游戏。如果你比较喜欢或者认同这个说法,可以去读罗伯特·沙因费尔德的《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他将手把手地教你成为一个随心所欲地玩人性游戏的高手。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演戏或者玩游戏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去?”
罗伯特·沙因费尔德说,你有一个普通目标和一个特殊目标。普通目标就是去玩人性游戏,得到人类进行所有游戏所获得的好处:乐趣、喜悦、娱乐、延伸、延展、探险等等。特殊目标是以独特的无限存有的身份,用你所选择的独特方式,进行这场人性游戏。
为了让这场游戏精彩、刺激、好玩、有趣,你制定了精密的游戏规则和程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忘记你是谁。这大概就是民间传说中“喝孟婆汤”的真实缘由吧——“忘记”,是为了从零开始玩游戏。
于是,你创造了一个真我的替身,作为这场游戏的主角。然后,你向替身隐瞒了你的真实身份和你全知全能的本性。接着,你设计了一个游戏场,并设计了其他玩家跟你一起玩这场游戏。另外,你还设计了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秘密指点你的向导。
这个游戏的主角,现在正在看这篇文章——也就是你一直以为的“你”。其他玩家就是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人。游戏场就是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秘密指点你的向导就是你的真我——真正的你。
从你来到这里的那一刻(也就是你的替身诞生之日)开始,你就开始隐藏自己无限的力量、智慧和丰盛。你的生活充满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你遇到种种麻烦、障碍和挑战,你有时面临绝境、束手无策,有时又欢欣鼓舞、绝处逢生……
我们每个人都在玩类似的游戏,只是主角不同、情节不同而已。有的人一直沉迷其中,直到死亡(肉体死亡)来临的时刻才想起真正的自己是谁;有的人玩着玩着开始觉得有哪里不对,好像遗失了某样东西,仿佛一切了无生趣,于是开始寻找人生的真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觉醒”或者“醒来”。
顺便说一下,你读到本文并非偶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除非你准备或者已经觉醒,否则你根本不会对这篇文章感兴趣。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知晓“我是谁”。
《与神对话》里有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从前有一个灵魂,它知道它自己是光。这是个新灵魂,所以急于想体验自己是谁。然而,在它的世界里,除了光,没有别的。每个灵魂都是崇高的,每个灵魂都是庄严华美的,每个灵魂都发着同它一样的灿烂光辉。这个小灵魂就像是阳光中的一支蜡烛。在最伟大的光——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中,它无法看见自己。
这个灵魂越来越渴望认识自己。有一天,神说:“小毛头,你知道你必须做什么来满足你这个渴望吗?”
小灵魂兴奋地说:“神啊,要做什么呢?我什么都肯做!”
神说:“你必须将你自己和我们其他的分开,然后你必须将黑暗召到你身上。”
小灵魂问:“黑暗是什么?”
神说:“你所不是的那个。”
于是,小灵魂将它自己与所有的我们分开了。然而,当它去到黑暗中时,却忘记了初心,反而哭喊道:“神啊神啊,您为何抛弃了我?”(一如我们遇到困境时的哭喊。)
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为何是它所是的样子,你为何是你所是的样子。在你被黑暗(“非你”)包围的时刻,请不要忘记你是谁。
这个寓言的下半段更精彩。
神对那个小灵魂说:“神的任何部分,只要你希望成为,你都可以选择去成为。现在,你希望体验神性的那一层面呢?”
小灵魂回答:“那我选择宽恕。我要体验我自己为神的那个称为完全宽恕的层面。”
“可是,没有谁需要被宽恕。我创造的一切是完美和爱。”神说,“看看周围,有哪一个灵魂是比你不完美的吗?”
小灵魂转身,吃惊地发现天堂的灵魂都在他周围。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因为他们听说小灵魂与神有一番不寻常的对话。
小灵魂想,他们都是那么地完美,我要宽恕谁呢?
这时,有一个灵魂走过来,友善地说:“你可以宽恕我。”
“宽恕我什么?”
“我会来到你下一次的肉身生活中,做一些‘坏事’让你宽恕。”
“但是,你本是如此完美,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那样做是因为我爱你。你不是想要体会自己的宽恕之心吗?我愿意协助你。我只要求一件回报。”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小灵魂兴奋地喊道。
“在我殴打你的时候,”那友善的灵魂说,“在我对你做你无法想像的事情的时候——就在那当刻……要记得我真正是谁。”
“噢,我不会忘记!”小灵魂答应道,“我会以我现在看到的你来认识你——完美无缺。我会记得你是谁,永远记得你是谁!”
这个故事有一点点触动你的心,或者唤起你呈封的记忆吗?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小灵魂,在每一次的投胎转世之前,都跟神有过类似的对话。我们也都对那个自告奋勇要来协助我们体验神性的某个层面而不惜做“坏人”或“敌人”的灵魂承诺过“我会记得你是谁”——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忘记了他是谁。
是的,你和我一样,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忘记了那个你最恨、最讨厌的人原是最爱你的人;忘记了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一个神圣的原因,以便你能知晓、选择、表达、体验和实现“你是谁”。
如果你不喜欢把你的人生看作一场游戏或者一场电影(电视剧),可以换个严肃的说法:当你(一个灵魂)准备进入到物质世界以肉身生活时,你先到你的灵魂档案里查看了你累生累世的肉身生活记录,然后选择了这一世的生活。接着,你放弃了对前世的所有记忆,并再次令自己忘记你真正的身份。这让你可以选择去做这一生你要做的那个人,去体验这一世你想体验的一切。
理解这一点,我就理解了罗伯特·李·坎普所说的——“一个灵魂在每一次生命中为什么会选择成为那张牌,对此,我们无法详知其中的细节或过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旦一张具体的牌被选择了,通过出生的日期,之后我们就会在一个架构明确的人生经历中行进,其中包含了实现最高成就和最高表现的个人计划。通过实现自己的人生架构,我们可以实际体验到宇宙大道生生不息的运行。”
领悟这一点,我就领悟了为什么我们只能成为我们的生命牌所代表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因为这是灵魂(真我)的选择,是灵魂(真我)渴望体验的道路和渴望实现的目标。所谓命运,就是一条我们自己选择要体验的人生道路。当我们顺应这条道路时,就会觉得快乐而满足;当我们背道而驰时,就会遭遇挫折和痛苦。
明白这一点,我就明白了《零极限》书中乔·维泰利和修·蓝博士那段令人费解的对话。
修:“每个人都有天赋。”
乔:“那老虎伍兹呢?”
修:“他在神性执导的戏剧里演出自己的角色。”
乔:“如果他去教别人打高尔夫球呢?”
修:“那他永远无法成功。他的角色是打高尔夫,不是教高尔夫。教高尔夫是别人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乔:“看门人也是如此吗?”
修:“没错!有许多看门人与收垃圾的人也热爱他们的工作。你不这么认为是因为你正在想象自己去扮演他们的角色,但谁也不能替代别人的角色。”
通过这段对话,乔·维泰利领悟到,关键在于不要抗拒你的角色。“我的角色是启发者,我写书的目的是要让人们觉醒,或者准确地说,是要让自己觉醒。”
乔·维泰利的领悟也是我的领悟。我或许向往成为像杨丽萍一样的舞蹈家,像彭丽媛一样的歌唱家,像韩金英一样的画家和丹道家,或者像玛格丽特·米切尔一样的作家。也或许我在这些领域的确能有所建树。但那不是我今生所要扮演和体验的角色(那可以是在过去或者未来,如果我想体验的话)——今生,现在,我的角色可能跟乔·维泰利一样,是启发者——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觉醒。也许,当我唤醒了自己,我也就唤醒了你。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有一个角色的。这个角色不是别人选派的,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许多人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神圣使命的,或者说我们的人生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目的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完成神圣的使命。如果这样想会让你更有激情或者感觉更好,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更有可能的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很多人都难以接受的,然而它却是宇宙给我们最了不起的礼物。借由让人生无意义,宇宙给了我们机会去决定任何事物及每件事物的意义。
《与神对话》里说,这就是你借之体验你选择你是谁的方法。神反复地强调:“别寻找人生的意义,或任何特定事物、事件或境况的意义。要赋予它一个意义,然后宣布与宣告、表达与经验、完成与变成在与它的关系中你选择是谁。”
我是谁?
我既是神圣整体的一部分,也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角色和要走的路。
我既是一个拥有无限力量而全知全能的灵魂,也是一个具有种种限制和束缚的肉体。
我既有神性中无与伦比的光明的一面,也有人性中无以言表的黑暗的一面。
无论是在“这不是我”中所列举的种种,还是“这才是我”中所列举的种种,这都是我。
我是一个拥有无限潜力和自由意志的创造者。我想什么就创造什么。我创造什么,我就成为什么。我成为什么,我就表现什么。我表现什么,我就经验什么。我经验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是什么,我就想什么。
循环于是完成。
亲,被我绕晕了吧?是不是有过山车的感觉?或者有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体悟?
“我是谁”没有标准答案。我之为我的目的就是——去忆起我是谁,去定义我是谁,去创造我是谁,去发现我是谁。
正如《与神对话》里所说的:每一个行为都是自我定义的行为。你的一切所思、所言、所行,都在宣布“这就是我”!
神还说:“我选择每一分钟重新创造我自己。我选择去体验关于我是谁所曾有过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我创造了你,以便你可以再创造我。这是我们的神圣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喜悦。这是我们存在的真正理由。”
亲,你对你是谁所曾抱持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是什么呢?去创造、表达和经验吧——那就是你。
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生命的奇迹!在过去的时光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
转载请注明:http://www.evwmh.com/zzbx/119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