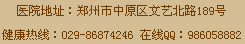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用药指南 > 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治疗目标自我呈现的发展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用药指南 > 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治疗目标自我呈现的发展

![]()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用药指南 > 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治疗目标自我呈现的发展
当前位置: 烫伤性皮肤综合征 > 用药指南 > 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治疗目标自我呈现的发展
杰克·恩格勒/文
李孟浩/译
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治疗目标:自我呈现的发展阶段(上)近年來,我嘗試要想通一組有關自我感發展的臨床議題。因為,有關這個夙稱「自我」之心理結構的本性和地位的問題,一直從兩方面來逼迫我展開思索。一方面,在我對精神分裂和邊緣症患者的臨床工作中,我發現他們深被自我主觀感受的病理障礙所苦惱。我因此確信從存在中發展一持續性、認同性和進行性之感受,有很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我教導佛教心理學和內觀冥想(vippasanameditation)的經驗中,也很明顯地看出攀附個人的持續性和自我認同,會導致長期的不滿和精神衝突。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刻,這個攀緣的心念讓我們跟整個宇宙作對,而這個宇宙中任何事物其實只能持續一剎那,也就是說「事物」並不真實地存在,在這千分之一秒所構成的時間次序中,真正存在的只是事件而已。現在我們從心理物理學知道內在宇宙確是如此,我們的意象、思想、感受和感覺每刻都在變動不居。
當治療師時,我盡一切努力幫助病人發展出內在的契合感、統一感和持續感,他們的悲劇往往就在於缺乏這種感受,才會有那麼多毀滅性的結局。當禪修老師時,我也是盡一切努力幫學生看穿他們經驗到的同一性和持續性知覺,其實是個幻覺,若照禪宗術語來說,就是了悟到無我。從這兩種傳統的心理學實習來看,我所辛苦搏鬥的議題就在於自我感的重要性和其命運。我曾特別關心過個人禪修時帶來的自我感,如何在禪修過程中消失,還有個人結束禪修時,又帶走什麼樣的自我感。
我思索這個議題時,發覺到有一堆困難,特別是心理動態和佛教心理學的「自我」和「自身」等關鍵詞,都在不同的文本脈絡中使用,而且對於自我的發展和一個穩定的自身結構如何形成,都賦予不同的評價(對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可參見Engler,a,此文側重在精神分析面)。這兩個術語很不幸地也在其傳統文脈中失去定位,造成它們很有可能變成廢話和口號。這讓我們更難整理出關於自我心理結構的核心議題。比如說,「超越自我」常被提出來當做學生習禪的目標,但這對心理動態導向的治療師卻不具意義。就治療師的立場而言,自我是個指稱規約功能和統合功能的集體性術語,在這個脈絡中,「超越自我」就意謂著要犧牲掉讓我們人性化的機能--這個心理結構能讓我們思考、計畫、記憶、期望、組織、愛戀、自我反思、分辨幻覺和現實、對衝動和行為進行控制。所以,超越自我等於在指涉一種跟機械人或木偶一樣的情境,很多損傷過自我能力的病人也是有這種退化或依賴的狀況。
從這個觀點來看,去參加禪修的人實在是需要自我組織達到相當的成熟層次,方能觀察到剎那生滅的身心過程,並發現那潛伏的恐懼、焦慮、羞辱、暴怒、沮喪、絕望、自我懷疑的情緒,甚至連出神狀態都包含在內。因此,臨床上而言,禪修應是增強自我,而比較不是超越自我。另一方面,自我心理學家總覺得從一切自我呈現中去除執著和消除認同的禪修目標,不是說絕不可能,就是有點怪異。但他們卻能了解到要去修正或捨棄掉那些窒礙的、適應不良的或過度成長的自我呈現,以及能去斷絕掉與客體的過度肥大或幼稚的聯繫,才能帶來心理成長的原則。
在跟這些議題奮戰的過程中,我已經發現只有「發展的模式」最適合用來解釋臨床資料和禪修資料,並且能讓我們整合這兩種觀點,視其關係為互補的,而非競爭的。從這個研究取向來看,我選了「精神病理學的發展層譜概念(developmentalspectrumconceptofpsycopathology)」做為出發點,因為它即將在臨床思維和實習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此概念的核心論題就是心理失調的病理發生過程會遵循一種發展性的年代次序,這一點可從心理動態-精神分析的研究(Mahler,;Masterson&Rinsley,)和發生-生物學的研究(Gottesmann&Schields,;Ketyetal.,)中,得到更多的例證。也就是說,人格組織和自我功能中不同病理質地的層次,都是從內向心靈發展(最重要的是客體關係的決定性方向)的不同階段裏的失敗、阻滯和退化而來。不管末梢病源學是天生的脆弱(Stone,)、發展性的精神創傷(Masterson&Rinsley,),或是兩者的結合,這一點也都同樣適用。
當我用禪修這個術語時,我所指涉的對象是佛教的內觀或「洞見」禪,內觀這個詞表示它的目標是洞察出心靈運作的本性,而非意識狀態的轉變。雖然內觀是由南傳佛教的傳統而來,它可說是禪修之定慧模式中慧見的純粹形式(Goleman,7)。修定是要把注意力長時間限定在單一的內在或外在對象上頭,修慧則是要把注意力擴展到各種瞬間生起的心理或物理事件。修定會領我們在三摩地或專注的境界進展中,進入從感官輸入撤離的過程,並有不斷精良化的寂靜感和福樂感。修慧則會領我們進入觀察所有感官輸入的過程,並看到一切現象都是無常、苦惱和非實體的。從佛教的觀點來看,修定是暫時把衝動功能和高一級的知覺和理智功能壓制下來,才能以免於衝突的運作功能,引發短暫的禪悅境界(註一)。但是,只有用修慧來帶動精神結構的持久性轉變,才能從一切苦中解脫出來(註二)(Nyanamoli,6)。
在現代來說,一般人都是用正念、無揀擇的覺察或只是注意的訓練,來描述內觀禪。這種實修是「用念念分明的覺察力,照見知覺流中確實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物」(Nyanaponika,3:30)。我們可用兩個技術典範來界定只是注意,一為注意力部署的特定形式,一為處理情緒影響的特定方式。就認知上來說,注意是限定在對意識中剎那發生的思想、感受或感覺,做出精確的記錄,卻不進而加工改良。也就是說,禪修者只是記下思想、感受和感覺的起起落落的順序而已。這就跟傳統的心理治療恰好相反,注意力都不放在它們的個別內容上。就情緒影響來說,這等於把所有的刺激都以平等心來注意,而不加以揀擇或檢查。這又再度跟傳統的心理治療恰好相反,注意力都要對所有知覺到的東西,保持免於任何反應的不動心狀態。也就是說,禪修者嘗試只是觀照任何刺激情境,而不加以任何偏好、評論、判斷、反省或解釋。如果對這些刺激產生任何生理或心理反應的話,也是一樣把它們記下來,然後納為只是注意的對象。即使在注意中有什麼差錯發生,像分心、幻想、白日夢和內在對話等,禪修者一旦察覺,也是一樣把它們納為只是注意的對象。所以說,內觀有三重的目標:認識個人的內在心理過程;開始有控制和修正它們的能力;最後能從幽暗和不受控制之心靈過程的制約中,得到解脫(Nyanaponika,3)。
客體關係理論和佛教的自我議題
雖然佛教心理學和客體關係理論對自我發展的評價有所不同,可是令人訝異的是兩者都以類似的方式來界定自我的本質。亦即,兩者都認為從內在生活和外在現實的綜合和適應過程中,會在作為「自身」之如是進行的存在感受裏,產生一種個人持續感和同一感。客體關係理論把個人持續感和自身性解釋為有關「自身」內在意象之逐漸分化的結果,以與客體的內化意象做出區別。而且,這些意象最後會凝結為一種混合的機制或自我的呈現(Jacobson,;Mahler,;Lichtenberg,;Kernberg,6)。南傳佛教的阿毘達心理學亦以類似的方式,把「我」感的出現解釋為認同過程的最終產物,在此過程中會學到認取某些構成我感經驗的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Narada,;Gunther,4;Govinda,4)。這個自身感就以「有身見(Sakkaya-ditthi,亦即個人信念)」來命名,正好精確地等同於客體關係理論的「自我呈現」。
所以,兩種心理學都認為在時空流變的意識過程中,「自我」感並不是人格與生俱來的,亦非天生內在於我們的心理構成中,而是從我們的客體經驗和互動類別中,逐漸發展演進而來。也就是說,「自身」是從我們對客體世界的經驗中「建構」出來。這個我們這麼當下認真當成「我」的「自身」,確實可以說是一個內在化的意象,一個混合過的呈現,而且這是由一種與我們有意味客體相遇後的選擇性和想像性「回憶」所構成(Bruner,)。事實上,兩種心理學都把自我看成是「每一瞬間都重新建構」的呈現物。雖然說是個呈現物,它可不是個固定的實體或圖表的制定,而是分殊意象的時光流程。每個意象都代表一個當下經驗中新的建構和新的綜合(註三)。但是,兩種心理學系統也都同意說我們平常不是如此經驗到自我感的。一般我們說的自我感其實是一種時間的持續感和同一感,一種人際互動中的一致感,一種他人認定過的持續感和一致感,一種我們察知他人認定我就是如此的知覺(Erikson,)。
這兩種心理學也同樣把自我的命運當成核心的臨床課題。從西元六世紀起,佛教的教義和實修就把無我原則和自我本性當成研究的核心。在精神分析思想的歷史中,我們可說是比較後期才發現自我感的重要性。因為,早期的精神分析思想是被發展理論、衝動和神經症的治療方式所佔據,還想不到自我結構的重要性(Tolpin,)。從歷史來看,對一不受伊底帕斯情結所苦病人的負面治療結果(Freud,),最後引人發現了客體關係發展和病理學有兩種差異分明的層次:(1)早期客體關係的失敗,特別是就自我和他人的分化和自我一致感的整合而言;和()稍後為此已分化和整合過的自我,來與受壓抑的衝突和伊底帕斯對象,進行防衛性的抗爭(Fairbairn,;Guntrip,、;Winnicott,;Kernberg,、6;Blanck&Blanck,4、9;Horner,9)。
罡利普(Guntrip)就曾指出這種發現「或許是本世紀對人格問題研究的重要發現」(1:)。近十年來,這個發現也引生了「發展性診斷層譜」的論題(Rinsley,),把各種臨床症候群都看成是在發展的特定階段中產生。這種對現在稱為邊緣情境和人格失調(居於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之間的運作層次)的新瞭解,事實上把現行的臨床注意力聚焦在分隔化-個體化的過程,這過程發生在前伊底帕斯發展期,此階段的主要課題是個別化、整合過、和與客體關聯過的自我分化,分化的成敗將是決定你循正常或異常進路來發展的主要因素。
就如我一開頭所說,臨床醫學和禪修體系對於自我命運的觀點似乎是全然相對反的。這就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從客體關係理論來看,最深層的精神病理學問題可以說是「自我感的缺乏」。因為,像幼兒自閉症、共生性和功能性精神病、邊緣情境等最嚴重的臨床症候群,正是在建立一致的、整合的自我(Kohut,1、7)或自我概念(Kernberg,、6)之過程中,所發生的失敗、滯礙和退化。雖然嚴重程度有很多不同層級,但這一切都代表了自身的失調(Goldberg,),沒有能力去感覺真實、一致性或「存在的實然(inbeing)」等一切。
從佛教觀點來看,最深層的精神病理學問題反而是「自我的呈現和自身性的感覺」。根據佛學者的診斷,苦惱的最深層根源在於保存自我的嘗試,而這種嘗試是徒然無效的和自我挫敗的。所以,精神病理學的最嚴重形式就是「我執(attavadupadana,亦即對個人存在的攀緣)」(Nyanamoil,6;Nyanatiloka,)。
在對於嚴重失調的臨床診治中,最重要的治療課題就是如何能夠「再成長」出自身的基本感受(Guntrip,),或是如何分化出和整合出一穩定的、一致的和耐久的自我呈現(Kernberg,6)。佛學者修行的治療課題則是如何「看穿」自我的幻覺或建構,如是如何解構掉那些「建築我們個人身份經驗的本質性認同」(Jacobson,:xii)。
所以,從佛學者的析來看,自我心理學所說的客體關係方向所達成的兩個偉大的發展成就-身份和客體恆常性-正是心理苦惱的根源。
也因此對我來說,在轉化過程中的自我命運變成一種實驗性的個案,以觀察這兩種治療目標是如表面上看來相互排斥?或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它們搞不好是相容的?的確,也有可能兩者之一會是另一的前提條件?最後這點也是我後來達成的看法。簡單來說,這個看法就是你必須先作為某人,才能什麼人都不是(youhavetobesomebodybeforeyoucanbenobody)。
我會朝這個方向走,是因為我有次幸運地無意中聽到一段臨床心理學家和亞洲禪修教師的精彩談話,他們是在討論兩人對於厭食症患者的各自診治方式,對我啟發很大。這位禪修老師是第一次來到美國,對於處理心疾的心理治療取向很感興趣。臨床心理師則在試圖描述一位厭食女性的高困難個案,因為她非常難以治癒。這位老師很快就投入個案的情況,問了一大堆病情和診治方面的問題。當心理學家結束後,我問這位老師為何對此那麼感興趣。他說自己在緬甸(Burma)的禪修中心,也碰到一位有相同問題的女性。此外,她也受苦於長期性的失眠。她要來學習冥想,可能是認為這會帶給她一些舒解。我就問他有教她嗎?令我驚訝的是他說「不」。
在六個禮拜裏,他只是讓她每天來抱怨她老公、小孩、雙親和生活的種種不公。他幾乎都是在聽而已,也有跟她說一些話,不過他並沒描述他所說為何。那麼,她「療程」的第一部分是經由人際關係的形式來導入。然後,他鼓勵她去睡,她短時間內開始把一夜的睡眠時間由四小時拉長到十八小時。她於是找他說「我睡夠了,我要來學習禪修。」他的回答又令我再度驚訝,因為他說「不,別修內觀,那有太多苦惱。」其實,她首先需要的是從心理煩燥中得到舒緩和平靜,以得到一些幸福和喜悅。這樣,她才能進而能夠容忍那深層的洞見,因為她看到的將不只是個人史中的興敗榮枯,而是她整個身心狀態都是在變動之中,並與苦惱有所關聯。既然修定能令人專一、寧靜和福樂,他便教她數息。她的睡眠時間漸漸便由十八小時縮短到兩小時,因為這就夠她睡飽了。在這時後,他才教她轉修內觀,開始叫她觀察身心事件瞬間流動,以直接體會到它們的極端無常性、挫敗性和無我性。她花了三個禮拜來將心打開,並證到初果。從此,她就再也沒有失眠過了。
這雖然不能算是一個臨床個案的研究。可是,它也宣示了一種精神病理學有不同層次的原則,而這些病理層次的根源也植基於心理發展不同階段中的扭曲、阻滯和失敗,並且需要不同的診治取向或不同型態的治療方法。實際上,自我心理學家也不再以涵蓋一切的意味來使用發展階段,而是以不同的「發展方向」(AnaFreud,)來思考,因為在任何既定時刻的心靈組織都是由這些發展階段之間的關係和心理功能來建構。在這些分殊的發展方向之中,我們有很好的理由來相信客體關係的方向,因為它可說是發展層次、心理健康、精神病理學和治療潛能中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決定因素(Mahler,;Kern-berg,6;Blanck&Blanck,49;Horner,9;Rinsley,)。
客體關係指的是有關於個人與人際對象之間互動經驗的程序與品質,這個人際對象特別是指原始撫育者(primarycaretaker)而言。而這些互動經驗也會被內化為「自身」和「客體」的雙重呈現,這些內心呈現都有情緒影響力,且會被燒錄下「好」或「壞」的記憶痕跡。這些多樣化的自身和客體呈現會逐漸凝聚成一份有關自身和客體的複雜圖表。於是,這些呈現被當成為內向心靈結構的發展基礎,也當然是自我感的發展基礎。所以,我認為以客體關係為主的發展觀點提供了一條線索,可以幫我們在治療性干預的模式中,找出佛學和心理動態系統的定位,並解釋它們的方法和目標為何有明顯的衝突。
就讓我從教學經驗的觀察中,舉出被佛教儀規所吸引住的學生類型,和他們通常練習時常遵循的過程。
禪修的臨床特徵
以內觀體系的古典階段來說,第一個特徵為「進展是相對地緩慢」。布朗醫師(DanielBrown)和我已在羅夏墨漬測驗的研究(請見第六章)中,確認了這一點。在連續三個月密集內觀修行的情況下,一大半三十歲新修團體的成員不管是在習後測驗或教師評量等方面,都沒什麼大的改變(註釋五)。後來,我在印度和緬甸的研究結果(Engler,b)也支持了這個發現,不過亞洲修行人的進展速度比較快,可是他們花在避靜環境中密集修行上的時間卻比較少。大部分的人只花了一、兩個禮拜的避靜時間,就體驗到初果(註釋六)。然後,他們就在家居生活的平常作息之中繼續修下去(註釋七)。
第二個特徵是西方學生會變得固著在可說是「經驗的精神動態層次(Brown&Engler,)」上頭。他們的修行逐漸被原始的思維程序和「非現實的經驗(Maupin,)」所盤據,比如幻想、白日夢、沉醉曲、意象、過往記憶的自發性回想、衝突資料的解禁、不停想來想去和情緒動盪的實驗都會增加(M.Sayadaw,3;Walsh,7、8;Kornfield,9;Kapleau,)。
第三個特徵是「對老師發展出強烈的移情」。這些現象通常看起來是寇哈特(Kohut)所說的鏡映或理想化的類型。一開始,在師生關係的脈絡中,學生會有找一個能接受和肯定他的「回映」來源的需求。接下來,學生會有和湧出「理想化」力量和寧靜感來源融合的需要(Kohut&Wolf,8)(註釋九)。有時候,我們會碰到另一種性質混亂的移情類型,完全被在全能感和貶抑感兩極之間極端快速的擺盪所吞沒。
我們要如何運用這些觀察成果?它們又要如何解釋呢?禪修老師通常把它們歸因於學生心態的一些因素。
一般來說,第一個因素是學生「缺乏能耐去發展足夠的定力」。因為,在能足以密切觀察身心過程,以修到內觀禪的開悟目標之前,先達到某種心不動搖和專一注意的定力程度,其實是必要的。這種把注意力穩穩地固定在當下浮現的身心事件之上的能耐,是南傳佛教領袖中尊貴的馬哈希大師(3)所強調的。以專業術語來說,這種能耐被稱為「近行定(upacara-samadhi)」,因為它是進入內觀禪諸階段的前提(Vajiranana,)。
此外,老師也指出學生會有「變成沉浸在意識內容,而不繼續觀照意識過程的傾向」。也就是說,學生會全神貫注於個人的思想、意象、記憶、感覺等等東西,反而忘了要別管內容為何,只管一直觀照所有身心事件的本質特徵:它們的無常性、它們無法滿足最簡便的欲望、它們缺乏持久的實體性、它們對也是刻刻變遷中之因緣條件的依賴性。當禪修者在早期修行階段時,首次進入他內心那寬廣、奇異、震驚中又令人興奮和迷惑的經驗世界中,就一定會產生這種黏著於意識內容的傾向。事實上,這種傾向可能和單純主體開始探索其它低度覺識(hypoarousal)狀態的情形,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這些狀態有催眠、夢幻沉醉和自由聯想。比如說,使用羅夏墨漬測驗的話,就可看出催眠對象的原始程序思維有類似的增加傾向(Fromm,Oberlander&Gruenewald,0),經歷精神分析的患者也是一樣(Rehyer,)。
也許,對內在心理氛圍的適應是任何意識之低覺識狀態的一般風貌,而與禪修的「特殊性」(Tart,a)沒什麼關係。由於西方文化中「治療學得到勝利」(Rieff,),也就有一種把治療和禪修相混淆的傾向,並用分析心理內容的方式來取代純粹觀照的方式。在東西方所有修行傳統中,這是一個典型的障礙。此外,某些文化因素也會助長這種黏著於意識內容的傾向。就跟一個文化的焦慮產生會在想像性參與的代價下,對於外在適應和現實範圍施加不少壓力(Hilgard,0)。同樣的,對於內在經驗流的長期適應也許是必要的。所以,西方學生在「禪修」時,未必符合禪修的形式意義。有人最近問一位亞洲來訪的內觀禪老師這些學生做得如何時,他回答說:「許多西方學生不是在禪修,而是在治療。他們無法深入正念之中。」
第三個因素是學生把禪修當成一個「孤立技巧的練習」,而不管許多其他重要的行為、動機、內向心靈和人際的因素,像正命、正業、正見和正念這些具治療作用的文化脈絡。這是因為禪修移植到西方時,已經從被佛教觀點和價值滲透過的文化脈絡中拔離出來,這些文化脈絡其實是屬於一個生活方式和整體性的訓練系統。佛教訓練或發展的八正道包括了正思維、正業、正命、正語、正精進,還有正念和正定。緬甸大師們也常常引用這些通向涅槃的正確途徑。
但是,我身為一個臨床訓練師,卻有不同的觀察。我看到這些學生在身份感和自尊上頭,有特殊的脆弱性和困擾。以最好的情形來說,這看起來是反映了認同形成的階段性和適齡性的發展問題(Erikson,、)。這一點特別適用於兩種熱衷佛教避靜的團體。一種團體是青年期後期(lateradol-escence)和快入成年期前期(earlyadulthood)的人,另一種團體是剛入或已在更年期的人(Levinson,8)。這兩個團體的人把佛教修行當成一種捷徑,好用來迅速解決他們生涯階段所面臨之必要的和恰當的發展課題。所以,他們常把佛教的無我教義,錯誤解釋為我不需要為認同形成的課題來奮鬥,或是我不需要努力去發現我是誰、我的能力是如何、我的需求是什麼、我的責任是什麼、我如何去跟他人來往和我應該或能夠為我的人生做什麼。也就是說,他們拿無我原則,來正當化他們對核心發展課題的幼稚性放棄。
如果以最糟的情形來說,這些個人身份感的脆弱和困擾是自身主體感的病理性困擾,
寇哈特可能會把這稱為「自身病理學」或「結構性缺陷病理學」(Kohut,1、7)。雖然在沒有臨床評估的情形下,這必須要小心一點。可是,我仍然懷疑有些學生是在接近自我組織的邊緣性層級中運作。在這裏,我是把「邊緣性」這個命名的精神結構性意味,指涉那人格組織和功能的「層級」,而非指涉一人格類型或角色失調(註釋十)。它代表了一種介於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之間的人格特徵失調群,這種失調是「穩穩地不穩定(stablyunstablr)」(Schmiedeberg,4),在兩種病症的連續體中具有症候性和發展性的轉移特性。這類失調群共享一個核心症候學,有相似的客體關係,也有共通的病理發生學。很多研究者相信在早期客體關係發展的分隔-個體化過程中的扭曲和阻滯,就是失調群的發生根源。根據某重要學派的想法,邊緣性人格組織的主要面貌便是「認同延伸(identitydiffusion)」(Kernberg,6)。
既然邊緣性人格組織中的整合已經失敗了,內在化的客體關係就會採取所謂的「分裂的客體關係單元」(Masterson&Rinsley,)。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自我、他人和外在事件都會根據快樂原則,被當成「全好(all-good)」或「全壞(all-bad)」的東西。如果它們看來是令人滿足的、能供應的,就是全好型;如果它們看來是很保留的、困擾的或剝奪人的,就是全壞型。所以,自我和他人的許多重要側面就這樣彼此主動解離開了,並由分裂化的原始防衛機制拆開,並讓人產生一種各側面都相對立或相衝突的態度。於是,這也導致了一種在相對立的自我狀態和自身及客體世界經驗之間,有相當令人混淆的替代作用:一下是神奇地有力量的、有益的和善良的;一下是令人困擾的、會吞沒人的、震驚的和邪惡的。這種全好全壞式的知覺性二分對立會伴隨著等級不同的「不完全自身客體分化(in
转载请注明:http://www.evwmh.com/yyzn/11758.html